我的母亲父亲陈述我整理
在年4月4日清明节前,谨以此文献给我最最亲爱的奶奶,由于今年疫情我的父亲不能亲自回去祭奠我的奶奶,以此来表达我们对奶奶的思念之情。由我的父亲陈述起草,我整理编辑。
对母亲的歌颂,对母亲的尊敬,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那首赞颂母爱的《游子吟》,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,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;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,表达了母亲对孩子体贴入微的深情。
我的母亲,年农历6月9日正值盛夏出生,母亲出生在一个农民家中,母亲生活的家庭当时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,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差,我姥爷清晨趁着天还没蒙蒙亮,把正在襁褓中的母亲抱到村外路边一片高粱地边就回村了,后来是一个我母亲称“七姑奶”的近门邻居路过此地,把母亲抱回了村,她把姥爷数落一通(抱回来时,母亲身上已经爬满了许多蚂蚁),是母亲的哭声惊动了七姑奶。
顽强的幼小生命在佃户家饥一顿,饱一顿,一直生长到十岁,生活才有了新的转折,她是以童养媳的身份来到了世代住在县城里的我家。祖上我家没有土地,历代都是靠小作坊磨面、卖馍,小买小卖为生,生活虽不算富裕,也算是比较殷实。母亲小小年纪从此脱离了农活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母亲从小勤快,全家非常喜欢,包括族家的长辈和平辈,有什么事只要喊她帮忙,她都乐意去力所能及的帮助,比如族家一位老奶奶眼睛失明,母亲经常扯着她到处走走,给她讲村里的故事,母亲的勤劳尤其是得到了我爷爷奶奶的疼爱,小小年纪会帮全家做饭、刷碗,13岁就跟着奶奶学纺线织布,做针线活。由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观念,母亲从10岁就开始裹脚,用布把正在发育成长的脚缠绕固定着,最终把十个脚趾头固定的弯曲变形,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小脚,蹉跎岁月母亲17岁那年与父亲成婚,第二年有了我的哥哥,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姊妹4人,在我四岁那年(年),我19岁的哥哥因病不幸早逝,在我印象中,哥哥已经娶了嫂子(至今哥嫂的模样我还记得),哥哥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可想而知,送走哥哥的白茬棺材,在家我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,欲哭无泪。
刚刚解放的县城,还不如现在一个村的规模大,我家因无耕地,房子也仅仅是三间茅草房,父亲被选为贫农代表,参加县政府组织的片区土地改革工作,为了全家的生计,磨面、做馒、卖馍,全落在了爷爷奶奶和母亲的身上,不足1.60米高的母亲,靠着一双小脚,一双勤劳的双手,整天起早贪黑忙碌着,父亲推着木制的独轮车,把粮食运到家就不管了,母亲喂驴、磨面,做饭,一家人四季的衣服、鞋帽的针线活也是母亲的,从我记事起,母亲为了家一天到晚都是忙碌,可我从来也没有听到母亲抱怨过。
我父亲姊妹三人,排行老大,弟媳妇脾气暴躁、强势压人,已成家不久就分家了,爷爷奶奶跟着父亲过,母亲是个贤惠媳妇,爷爷奶奶疼爱有加,记得有一次做饭的时候,母亲烧地锅,弟媳妇灶台添水做饭,趁母亲将锅加热时候,故意将一瓢冷水猛泼向锅内,顿时炽热的水滴溅落到母亲身上,母亲一声不吭,奶奶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奶奶刚五十出头就得癌症,母亲伺候奶奶比姑姑还周到,直到临终。我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
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在本族中长辈们喜欢她,平辈们有什么高兴的事、委屈的事都愿意和她交流谈心,我们族家在城西关虽不是什么名门望族,但也是个大族户,平日里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,母亲在族家和邻居中从不说这家倒那家,也从不评判别家的事,母亲跟奶奶学了一手治疗火眼(红眼病)的绝活,不吃药、不打针,通过按摩眼眶周围,在眼角扎针放血,能治好眼疾,每到炎热夏季,到了下午,到我家找母亲治眼病的人可多了,母亲再忙总是放下手中的活,给人家治病,从来没有收过谁家一分钱,母亲还会刮痧、拨火罐,为成年人和小孩治病,在我的记忆中,我们全家老老少少一年四季很少找医生看病(奶奶除外)。总之,她是一位端庄贤淑的好妻子,料理家务、赡养老人、照顾丈夫和孩子,同时还是一位睿智、尽责,顾全大局,肯为别人着想,有着高尚品德的奇女子。
旧社会的母亲当她在危难的时候碰到了好心人(七姑奶),当她在困苦时遇到了好人家,当她长大成人后得到了好丈夫,当她晚年时有着孝顺的儿女(不包含只贪图奶奶恩泽的人)陪伴她左右,96岁无疾而终,安详的被圣洁的主接到了天堂。
在坎坷的经历中,在生活的历练中,一个不识字的女子,含辛茹苦抚养长大她的儿女们,母亲善良、睿智、孝顺,从骨子里渗透的遗传基因影响和教育着他的儿女成长,儿女们们不管走到哪里,母亲的爱就像一条慈绳爱锁连在一起,她的儿女们也必将像她那样将爱锁传承下去(还是不包含诋毁奶奶,只贪图奶奶遗留恩泽的人)。
土地改革以后,政府又分了我家三间草房,和少许自留地和房产宅基地,因无钱建房,宅基地直到今天还在空着,六间草房三间住人,三间做灶台和磨坊。继续以作坊行为维持生计,不同的是不再卖馍,改为只为当时的市民和政府机关部门加工面粉和碾米,由于父母亲做事实诚、认真,给县粮店加工面粉碾米从不掺假、缺斤短两,并且米面的质量好,深得粮店领导的信任,逐渐加工米面的业务量也大了,可苦了母亲,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已经有早自习了,往往是鸡叫三遍,天已快亮了,母亲已经磨出了两大筐面粉,正好叫醒我去上早自习,在公家粮店上班前,我父亲就早早的把米送到了粮店门口,一年四季刮风下雨从来没有耽误过,白天母亲又和父亲一起淘洗晾晒粮食,还要为一大家子做饭,到了晚上,下了晚自习,母亲就在油灯下纺线等到我睡下了她才去睡,由于业务量大,我家喂的小毛驴确实不堪重负,星期天母亲就动员儿女们帮她推磨,就给我们的小毛驴放假一天,做儿女的能体会到父母的辛苦,都是很自觉的争着抢着多干些活,多推几圈磨,这时母亲总是高兴的说,一个蛤蟆四两力。夏天到了,下午放学回家,我总是先做完作业,然后就拿起镰刀、箩筐到田野里去割小毛驴爱吃的青草,割的多了,拿不动了就回来和父亲一起抬回家,父亲是个脾气直爽、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人,母亲是个性格温柔、胸怀宽广的人,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,有一天母亲把一大袋细米糠当做粗米糠卖了出去(价格不同),父亲回到家后,赶紧去追也没有追回来,沮丧的回到家里暴跳如雷,也惊动了邻居,我当时吓得也不敢吭声,母亲一句话也没说,可父亲还是没有骂母亲一声,更没有打母亲一下,在我们做儿女的记忆中,从没听到过父母亲对骂和吵架的事,在我的印象中,从我能记事起从来没有被父母亲打骂过。
姐姐回忆,我当时上小学,她上初中,母亲半夜就起床磨面,听到母亲用两双小脚蹬着半机械化的筛面工具,咣当咣当声音时,姐姐就睡不着觉了,起来陪着母亲,母亲催促姐姐去睡觉,姐姐坚决不肯,陪着母亲在磨坊油灯下看书,在姐姐的记忆中,母亲很晚才睡,几乎没睡一样,在我记忆中,姐弟俩从没因吃饭晚,上学迟到过,母亲从没说过累,也许就是那根慈绳爱锁支撑她的重担吧。
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,最艰苦时候,在县城没人供应练市一两八钱,加工面粉明显少了,父母省吃俭用供应我姐弟上学读书,她吃包皮馍,给我们做白面馍,那个岁月白面馍过年时候才能吃上,杂粮面能够吃饱就很不错了,尽管这样,母亲每次看到逃荒要饭的人到我家门口,就是自己少吃一点,也必须给要饭的一点,从没有让要饭的人空过手,有稀饭时候给人家盛一勺,有馍吃给人家掰一块,三年自然灾害,农村更是艰苦,母亲把我姥爷接到家一住就是三年,但是姥爷身体不好,每天晚上咳嗽,有时候能把我咳醒,就这样父亲不乐意让姥爷住我家。
尽管三年的自然灾害,给才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带来了灾难,人们缺少食物,外部有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反动派的捣乱破坏,但依靠社会主义人民的空前团结、万众一心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,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落后的中国农业,快速的向电灯、电话、洋犁子洋耙转化,小小的县城年就有了自己的发电厂供街道和县机关、县面粉厂供电,从此我家不再经营磨坊了,我家也由副业队转化为农业队,父亲把小毛驴卖了,买回家了几只杨和两头小猪,父亲和爷爷在农业队经营农活,挣工分,母亲在家做家务,养羊、喂猪、喂鸡,我放学后做完作业,仍然割草喂生产队的牛,小小年纪每天靠割草也能挣两分,星期天能挣上四分,当时成人劳动一整天才挣10分,在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年代,儿女能体谅父母长辈的辛苦,长辈非常满意懂事的儿女,我从四年级开始就一直是班里的少先队大队长、班长,一家其乐融融,每逢放暑假,母亲就打起包袱,带领我们姐弟三人,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就上路奔走四十里路到我姥爷家收秋,一路上,走走停停,渴了喝几口路边沟里的清水,直到中午才到姥爷家,开学时舅舅赶着牛车,送些粮食、芝麻叶等好吃的东西送我们回到县城,一年又一年,每到年终前家中卖一头猪和几只羊,留下一只羊自家享用,至今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卤面的香味,在那个年代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,仍没有富裕的钱拿出来翻建漏雨的茅草房,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年秋天,16岁的我与邻居家的小伙伴一起,带着被子和干粮,到距离县城30里路的大山里住在一个远方亲戚家,割黄笔草(一种可以盖房子用的硬杆草),每星期回家一次,带些母亲早就预备好的干粮,一直割草到冬天,快下雪了才回到县城家中,兄弟两个硬是不花钱割了翻修三间房子所需的干草,父亲一年四季在生产队挣工分,炎热的夏天,几乎每天中午下工后,也不休息,马上到街上的面条铺继续下力气给人家压面条,一中午的劳作,不发工钱,只换来足够全家人吃一顿的好面条,我每逢放学后,看到父亲总是满头大汗在那里绞面条,顺便把换回来的面条带回家。幸福是靠劳动创造的这一理念,牢牢扎根在儿女的心灵深处。
光阴似箭,岁月如梭,在父母哺育和教养下,姐姐高中毕业,经过自己的努力被县城录用为正式工人,年珍宝岛正在打仗,经过父母的同意,我报名应征入伍,第一次坐火车,经过几天几夜到了军营,第三年被选拔为空军飞行员,在航校学习期间也是我离家入伍的第四年,母亲实在是挂念儿子,吃不好、睡不好,她也是第一次坐火车,由县城坐汽车、路上颠簸四个小时才到了驻马店火车站,拿着我往家里写信的信封(信封上有我航校的地址),走一路问一路,终于到了航校所在地,当我到车站接母亲看到阔别四年的母亲时,没想到四年前一头黑发的目前如今满头白发,母亲看到儿子长高了,而且走的是正路,母亲放心了,当校友到招待所看望母亲时,母亲露出了灿烂的笑容,和母亲短暂相处的几天里,母子俩有说不完的话,印象最深的是:“别想家,好好学习,也别挂家。”从航校送走了母亲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认真学习、刻苦训练之中,年秋天,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海军第一航空学院。飞过初级教练机和高级教练机,被正式分配到航空部队,年女儿出生,当年我跟随部队驾驶战机飞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线机场,时刻准备与敌人作战,当时母亲知道我上了前线,她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,没有告诉我女儿出生的事,直到年的秋天我才见到我的宝贝女儿,事后我才知道,女儿出生的时候,是母亲在妻子跟前守候一夜,是母亲找的接生婆当启明星升起的时候,我的女儿降生在我自己家的老屋里,是母亲的精心照料和呵护保证了母女俩的健康。
年冬去春来,万物复苏,农历2月25日父亲因我家分三间草屋(祖上遗留下来),被本族家弟媳妇谩骂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,噩耗传到部队,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,第二天傍晚才赶到家中,从此我的人生历程也发生了转变,当时因我弟弟也在外地工作,姐姐也不经常在家,地方大队干部也站在对方利益上,不懂法,我父亲性情耿直,健壮的身体一下子就没命了,63岁的母亲突然失去了老伴儿,此事极大的刺激了我,处理完父亲的后事,回到了部队,担心母亲还操心姐姐,妻子一直跟有关方面打官司,由于休息不好,直接影响了平时的飞行训练,年一次海上夜航科目,脑袋异常,出现错觉,不得已中途返航,平安落地,一下飞机汗珠浸透了飞行服。年停飞,年转业到地方工作,从此姐弟三人哪家需要帮忙,母亲都乐意去做,成了儿女们的“香布袋”(事到如今,儿女们有的知道感恩,有的却在一味地指责、诋毁我最最亲爱的奶奶,我为奶奶抱不平)。
平凡又不识一个字的母亲,坎坷的经历和机遇造就了她是一位有盼望、有信仰的伟大母亲,经邻居引荐母亲80岁的时候开始信仰基督教,86岁一个人还拄着拐杖去教堂走礼拜,一年四季几乎很少缺席,而且每周末走礼拜的时候早上还禁食,从不迟到,母亲的虔诚令儿子感动,在家时候我经常听到母亲为自己祷告,为儿女祝福,日复一日,90岁以后,母亲因一个小意外摔了一跤,从此再也不能自己走路了,眼睛也有了白内障,我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,年农历五月初二中午母亲依偎在我的怀里去了天堂,母亲96岁无疾而终,这也许是母亲与我生命之间或许存在这相依存的关系吧,正如耶稣使徒保罗说:“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”,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,母亲庄严、慈祥的容颜永远活在我的心间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gdnxd.com/ways/14079.html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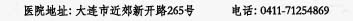
当前时间:
